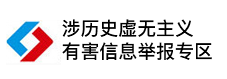□甘霖
春天,看花草萌发;夏天,听溪河豪迈;秋天,数萧萧落叶;冬天,揽飘飘雪花。西关街如同一位饱经世事的老人,一切在它面前都显得那么闲适、宁静、安祥。虽然,它的衣衫很破旧,它的面容很苍老,它的肌肤很暗淡,甚至构成它血肉的小巷那么曲折狭窄——屋舍已现断壁残垣,墙面早就斑驳晦涩,檩椽蒙有累累尘埃,但这丝毫不能掩没它独有的风韵。
它是秦巴腹地竹溪县的一条老街,其东连荆楚、西指秦川、南临溪河、北倚五峰,身影狭长而又纤细,在莽莽崇山峻岭之中,似乎显得太不起眼,也太微不足道。然而,就是这条衰败破旧的街道,曾以一种海纳百川的气概,将竹溪与半个中国紧紧相连,为无数流离失所的人们提供庇护、送去慰藉。500年前,因灾害与战乱,百万流民涌入荆襄。静谧的竹溪从此苏醒,向四面八方的人们,敞开了温暖的怀抱。它慷慨地献出山川河谷,以其肥沃的土壤、富饶的物产,给苦觅活路的人们送去了新生的希望。到1476年,竹溪置县时,流民达11.3万余人。可以说,竹溪因流民而立起门户,西关也是应流民之需而诞生。于是,在竹溪毫无保留地为流民献出一切的时候,西关已不再是西关,而是一个动荡时代的缩影,是四方流民交融的遗存,是万千民众朝觐的精神家园。
在众多的竹溪人眼里,西关街就好像一块墨玉,有着说不完、道不尽的美。它静静地依偎在款款东去的竹溪河畔,近可览五凤飞云,遥可观画屏烟雨,俯仰之间,令人生出许多遐想。可是,当我们领略过平遥古城的奢华、凤凰古城的空灵、丽江古城的精巧、大理古城的典雅后,再回过头来看身边的西关街——那灰黑陈腐的色调、狭窄逼仄的巷道、低矮无奇的民房、门板紧闭的铺面,多少会使人怅然若失。为什么我们魂牵梦绕的西关是如此寒酸呢?这一疑问,使得众多的赞誉之人立马变得惶恐起来。难道西关街真的那么不堪吗?不,当然不。等浮躁的心宁静下来,你再置身恍若隔世的西关,或许,很快会收回先前的鄙夷和轻慢。兴许是境由心生吧!此刻,你眼里的西关街简直换了容颜:屋舍相勾连,呈现出鳞次栉比的壮观;商铺肩并肩,显示着接踵而列的气派。还有那镂空雕琢的窗棂,那翘首昂扬的飞檐……每一幅画面,似乎都含着某种神秘的表达。轻轻抚摸风餐露宿的古墙,静静体味质朴醇厚的气息,细细搜索披荆斩棘的印迹,你不免会陷入深深的思索。突然间,你的脑海里,眼前那空空如也的街面,竟然挤满了熙熙攘攘的人群,它们或提着篮,或挑着筐,或背着山货,往来穿梭于各个门店之间,用各种不同的口音、和颜悦色的神情,洗尽拓荒者满身的酸楚与艰辛。街之普通,民之憨厚,相得宜彰,共同承载着溪城的喧嚣与繁华。
风雨飘零500年,今天的西关街,早无往日的光华,已是人少街空。穿行在落寞的街道上,寂寥的风迎面吹来,让人惆怅地想起那句古诗:“黄鹤一去不复返,白云千载空悠悠。”曾经商旅匆匆的古道,经不住岁月的侵蚀,无奈地看着蜘蛛漫天吐丝,任由它网罗一个个痛心的叹息。就连那铺就流民梦想的青石板,也在岁月的蹉跎中,完全沦为书里的记忆。曾经声名鹊起的会馆,在悄无声息中慢慢地坍塌,残墙上的狗尾巴草,频频对着长天招摇,茕茕孑立的身姿,映照于空旷的院落,在青砖黑瓦上投下一片凄凉。曾经寄予乡愁的土音,在生命的轮回中渐渐隐去,南腔北调的对话,已成西关上空的绝响,一切来自先祖的印象,最终蜷缩于泛黄的家谱之中。当时光从彼时进入此时,流民由客民变为原住民,西关街在完成历史使命的同时,逐渐走向衰败与没落。人们不禁要问,它真会彻底死去吗?不,不会的。历史发展到今天,它从中心走向边缘,从兴盛迈入落寞,几如垂暮之年的老人。然而,随着西关街改造工程的启动,它的未来将不是倒下,而是涅槃般的新生。
如今,有着流民生存繁衍的栖息地、流民发展变迁的活化石、流民坚忍不拔的纪念碑之称的西关街,其精神和底蕴,已深深融入每个竹溪人的血液,相信不管是现在,还是将来,必能鼓舞着一代又一代的流民后裔们,在通往幸福美好的康庄大道上,谱写出更加华美的篇章!
《十堰晚报》编辑点评:一条老街,承载着一段辉煌而又沧桑的历史。问起竹溪人,没有人不知西关老街的,这里留下斑驳暗淡怀旧的光影,故而西关街的拆迁,牵动着多少竹溪人的情愫。我们可以透过文字触摸那些厚重的历史,也可以将老街镌刻在深深的记忆里。拆去的只是那些残破的院落,拆不去的是蕴藏其中的人文情怀和文化底蕴。
( 责任编辑:admin 新闻报料:2729868 )